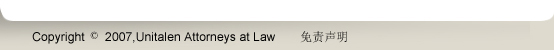|
最近,笔者在学习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专利侵权判定指南》的过程中发现,北京高院在该指南在第一部分发明、实用新型专利权保护范围的确定中关于权利要求解释方法部分对所属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这一专利领域中非常重要的概念给出了定义。这应当是法院界首次对这一重要概念给出了自己的定义,无疑对于专利确权以及侵权判定具有重大意义。
“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或称之为“所属技术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或者“本领域技术人员”,对应英文为“person skilled in the art”或者“skilled person”,这一重要概念贯穿整个专利实践,它就象一个无形的影子,站立在专利法的各个法律条款之后。可以说在讨论专利法相关的各个环节时,这一概念几乎都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判断一项专利技术相对于现有技术是否具备新颖性和创造性必须站在本领域技术人员的基础上;判断一项专利是否充分公开,必须要判断该专利技术是否能够由本领域技术人员实现;判断一项权利要求是否能够得到说明书的支持应当看权利要求所要求保护的技术方案是否是本领域技术人员能够从说明书充分公开的内容中得到或者概况得出的方案;解释权利要求应当从所属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的角度进行①。
笔者认为引入“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的原因在于:专利文件是用语言文字描述的技术内容,虽然技术内容本身是客观存在的,但语言文字则固有其不确定性和模糊性,由于不同人的知识背景不同,可能会存在不同人对同一问题存在不同理解。正如同样一个世界会在不同人的眼中幻化出万千不同的景像一样,只有确定统一的判断主体才能有助于体现专利制度的公正性和客观性。
一、关于“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概念的历史沿革。
在我国《专利法》制定伊始,其条文中就出现了“所属技术领域技术人员”这一概念。1985年4月1日开始施行的《专利法》第二十六条规定:“说明书应当对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作出清楚、完整的说明,以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能够实现为准;必要的时候,应当有附图。”这一条款在历次的《专利法》修改中没有任何的变化,即《专利法》第二十六条第三款,也就是业界所称的“充分公开条款”。在我国《专利法》中除了在该条款中出现了“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这一概念外,其他的法条中并未再出现这一概念。而无论是在《专利法》还是《专利法实施细则》中都没有对“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的含义作出更多的解释。
《专利审查指南》是由专利局制定的部门规章,是对《专利法》及《专利法实施细则》的进一步的细化。在历版的《专利审查指南》中都对“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这一概念做出了解释。但有一点值得注意,虽然在《专利法》中仅在“充分公开”条款中提到过“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这一概念,但在《专利审查指南》中,在关于“充分公开”条款的章节中却未对这一概念作出定义和说明,而是在“创造性”条款的相关章节中对此作出定义,并且明确说明“充分公开”条款中“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的含义适用于“创造性”部分中的规定。
最初的在专利局内部实行的《审查指南》中,规定“在评定发明是否具有突出的实质性特点时,引用了发明所属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这一概念,他是指发明所属技术领域中,具有该专业中等技术知识的技术人员。他的技术水平随着时间的不同而不同。在同一时间,不同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的知识水平也不尽相同,发明所属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与审查员不同,他是为了公正地评定发明创造性而设想出的一种人。”这个关于“所属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的规定更多的是在说明为什么要设置这一假想的“人”,对于其应当具备的实质性条件几乎没有涉及。
1993年《专利法》和《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一次进行修订,相应的,专利局也修改了《审查指南》,并对社会公众公布出版。其第二部分第四章2.2节中规定:“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与审查员不同,他是一种假想的人。他知晓发明所属技术领域所有的现有技术,具有该技术领域中普通技术人员所具有的一般知识和能力,他的知识水平随着时间的不同而不同”。上述规定开始触及到了“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所应当具备的实质性条件。然而上述规定中“他知晓发明所属技术领域所有的现有技术”的标准却给审查员带来了困扰。例如,在对专利申请是否公开充分的判断中,如果认为本领域技术人员知晓申请日之前的所有的现有技术,那么专利申请说明书中只需要记载与本申请发明点相关的技术内容即可,而不必记载任何现有技术。而能够恰巧地知道该专利申请所基于的那一份或者几份现有技术的文件并且又恰巧地能将上述几份文件从全部所知的现有技术中提出来与该专利申请中的发明内容互相结合、从而得到该专利申请请求保护的技术方案,这对于社会公众来说无疑是过高的要求,这样的规定也会使得“充分公开”条款沦落成一纸空文。
2001年国家知识产权局对《审查指南》进行修改,其中,第二部分第四章2.2节中规定:“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也可称为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是指一种假设的“人”,假定他知晓申请日或者优先权日之前发明所属技术领域所有的普通技术知识,能够获知该领域中所有的现有技术,并且具有应用该日期之前常规实验的手段和能力,但他不具有创造能力。如果所要解决的技术问题能够促使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在其他技术领域寻找技术手段,他也应具有从该其他技术领域中获知该申请日或优先权日之前的相关现有技术、普通技术知识和常规实验手段的能力”。这样的规定显然是对93版《审查指南》中“他知晓发明所属技术领域所有的现有技术”做出了实质上的修正,2001版《审查指南》中更加侧重在“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获得知识方面的能力。
上述关于“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的解释在2006版《审查指南》以及2010版《专利审查指南》中均基本沿用了下来②,可见,上述规定对于实践来说基本上是合理的、行得通的。
二、欧洲专利局《审查指南》中对““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的规定:
在欧洲《审查指南》对专利申请是否充分公开的规定中,对“所属领域的技术人员”的定义作了特别的规定③: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被认为是普通技术人员,他不仅知道专利申请自身的教导以及专利申请中的引用文件,还知道在专利申请的申请日时的普通技术知识,他具有由其支配的常规作业和实验的手段和能力,这些在所属技术领域中是常规的。
根据欧洲《审查指南》中对“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的规定来看,其定义基本上与我国《专利审查指南》中的对该概念的定义相同。这也体现了我国在专利审查标准上与欧洲专利审查标准相类似的特点。
三、“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应当具备的知识和能力。
我国《专利审查指南》规定“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具备的知识为“知晓申请日或者优先权日之前发明所属技术领域所有的普通技术知识”,具备的能力为“能够获知该领域中所有的现有技术,并且具有应用该日期之前常规实验手段的能力”。其中,何谓“普通知识”对于理解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的概念非常重要。
虽然我国的《专利审查指南》中提到了“普通技术知识”,然而却并没有对于何为“普通技术知识”进一步给出明确的解释。
同样用“普通知识”来解释“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是欧洲专利局。欧洲专利局《审查指南》④规定,普通技术知识包括基础手册、专著和教科书中公开的信息。经全面检索后而获得的信息不能被看作是普通技术知识的一部分。但如果发明所处检索领域很新,以至于无法从教科书中查找到相关的技术知识,那么在专利文献或科技出版物中所包含的信息也可能构成普通技术知识。但是,即使是在新的技术领域,也不是任何专利文献和科技出版物都可以构成普通技术知识,是否构成普通技术知识的关键在于能够合理推断出所述专利文献和科技出版物中记载的内容被所属领域的技术人员所广泛获知。
基础手册、专著和教科书中公开的信息通常被认为是公知常识。由此可见,“普通技术知识”的范围比现有技术的范围要窄的多,比公知常识的范围又宽,并且“普通技术知识”的范围与其所处的技术领域有非常大的关系,对于发展比较快的新兴领域,“普通技术知识”的范围涵盖的就要大一些。其设立这一标准的宗旨还是在于对于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其相关信息是否能够被广泛获知。或者,简单的来说,普通知识是这个领域的技术人员通常情况下必然知道或者必然能够知道的。
四、“所属技术领域技术人员”在不同条款中的适用
前面曾经提到,虽然我国《专利法》中仅有“充分公开”条款提到了“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这一概念,但在《专利审查指南》中这一概念却是在创造性部分被定义的。同时,《专利审查指南》第二部分第二章第2.1节关于专利法第二十六条第三款的规定中明确规定“关于‘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的含义,适用本部分第四章第2.4节的规定”,即创造性中的规定。在其他涉及“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条款的相关规定中,再没有提及这一概念的含义。由此可见,我国现有规定对于“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这一概念在不同的条款中的含义应该是完全一致的⑤。
然而,在实践中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即同样一篇专利文献,在判断创造性时可以作为对比文件,但在判断充分公开时就不允许专利权人将其引入背景技术,这显然与这种“一致”是相违背的。审查实践中,通行的做法也是:在创造性判断时,只要是现有技术就可以作为评价创造性的对比文件而不论该技术信息如何获得、是否存在获得该技术信息的启示;但在充分公开的判断中却不可以随便将现有技术公开的信息作为解释本申请公开内容的证据,除非是在本申请的背景技术中曾经明确提到过的引证文件或者公知常识、普通知识等信息。
究其原因,我们可以从1. “充分公开”与创造性条款的不同侧重点,以及2. “偶然性”与“必然性”的差别两方面来理解。
1. “充分公开”与创造性条款的不同侧重点:
专利申请说明书的充分公开以及具有创造性高度是专利权获得国家强制力保护的“对价”。虽然“充分公开”和创造性条款都与专利权是“以公开换垄断”的原理相关,但这两个条款的侧重点却是不同的。
充分公开条款希望达到的目的是,所有本领域的技术人员在阅读了专利说明书之后都可以将该专利的技术方案再现,无论是保护期结束之后的实施还是在其基础上进行进一步的发明创造,这才是真正的公开。如果仅仅是部分的技术人员---如某些具有高学术水平的人员或者某些恰巧阅读了某篇现有技术文件的人员---才能实现其技术方案,那么会造成以下两种不利因素:第一,专利权人获得的垄断性的权利是针对社会全体公众的,而能够从中获益的却是部分公众,这显然是不公平的;第二,如果我们承认一些偶然的因素可能造成某些人能够实现而另一部分就不能实现专利文献中的技术方案,那么我们就将很难在什么样的东西必须被包括在专利说明书中这一问题上划出一个清晰的分界线,那么这个问题将会变成一团乱麻。因此,《专利法》第二十六条第三款所述的“充分公开”应当是针对所有本领域的技术人员,要求每一个本领域技术人员(当然会对这样的“人”应当具备的知识和能力作出一定程度上的要求)在阅读了专利说明书之后都能实现其发明创造。
而创造性条款希望能够达到的目的是,得到专利制度垄断性保护的技术方案是专利权人真正对现有技术做出贡献的部分,或者说专利制度力图保护的是第一个做出贡献的人。理论上,这里面的“第一”是相对于全体的本领域技术人员而言的,不应该受到偶然性因素---如某些技术人员恰巧不知道这样的现有技术---的影响,即专利法要绝对杜绝对于一部分人来说具备创造性而对另一部分人来说不具备创造性的情形出现。
2.“偶然性”与“必然性”的差别
通过“充分公开”和创造性条款的立法本意及不同的侧重点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结论:是否“充分公开”考察的是一种必然性---所有的本领域技术人员都能当能够实现该发明;与此相对应,创造性考察的是一种可能性---只要存在本领域技术人员在现有技术的基础上能够不需要付出创造性劳动就能获得该技术方案的可能性,就不应当认为该技术方案具备创造性,这从各国对现有技术公开的要求中也可见一斑---出版物不受发行量多少、是否有人阅读过、申请人是否知道的限制。
这种“必然性”与“可能性”的不同,使得上述两个条款在面临本领域技术人员这样一个群体的时候,一个关心的是每一个个体所应当具备的能力,而另一个关心的是整个群体中包含的各种的可能性。即,虽然我们在上述两个条款中用到都是“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这样一个主体概念,但其实质是,在“充分公开”条款中“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是一个个体性的含义,而在创造性条款中“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是一个群体性的含义。当考虑的是一个个体的必然性的时候,我们当然要求说明书对于所采用的现有技术做出明确地说明或者给出明确的指引,用以在制度上保证每一个“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都能够实现该发明。当考虑的是一个群体性的可能性的时候,不需要每一个“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都能够获得某具体现有技术,只要存在某一个“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能够获得的可能性就足以了,因此各国甚至都不要求该出版物实际上真正有人阅读过。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存在”就意味着被“获得”的可能性,在证明“可能性”这方面“存在”就已经足够,不再会要求其他。
五、不同法律条款中关于“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不同含义的解决
有研究认为,应当将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所具备的能力分为5个要点,并且明确:在各个不同条款中,“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所具备的能力要点是不相同的,例如在创造性判断中就应当具备第2个能力要点“能够获知该领域中所有的现有技术”,而在充分公开判断中则不应当具备这一能力要点。有人认为这实际上是承认了“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在不同的条款中的含义是不一致的。然而笔者认为,在专利实践中应当对“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有一个统一的概念,这样才能有一个一致的参照系。在处理不同法律条款中对“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的不同能力要求时,可以在各法律条款的具体适用部分对“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的能力要点是否做出要求做出特别的规定,这样就完全可以解决不同法律条款中对“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的不同要求。
反观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专利侵权判定指南》中对“所属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的定义:“所属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亦可称为本领域的技术人员,是一种假设的“人”,他知晓申请日之前该技术领域所有的普通技术知识,能够获知该领域中所有的现有技术,并且具有运用该申请日之前常规实验手段的能力。所属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不是指具体的某一个人或某一类人,不宜用文化程度、职称、级别等具体标准来参照套用。当事人对所属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是否知晓某项普通技术知识以及运用某种常规实验手段的能力有争议的,应当举证证明。”。可以看出,《专利侵权判定指南》对“所属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的定义没有审查指南中所规定的全面。笔者认为,无论是专利侵权还是专利确权,对于“所属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也应当有同一的含义,这样才能为不同的判断主体(原告、被告和法院)提供同一的判断基础,否则会产生审判中的不公平。然而,北京高院在对“所属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给出定义之外,另外还规定了在审判中确定“所属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的辅助判断标准,即“所述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不是指具体的某一个人或某一类人,不宜用文化程度、职称、级别等具体标准来参照套用”。这无疑会对司法实践中确定“所属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给出比较明确的指引,有利于统一判断标准。另外,该《侵权判定指南》中还进一步明确了有关普通技术知识以及常规实验手段在举证责任分配上的原则,有利于司法实践中争议问题的有效解决。
注:
①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专利侵权判定指南》:一、发明、实用新型专利权保护范围的确定:(三)解释方法:10、解释权利要求应当从所属技术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的角度进行。
②说“基本沿用”是因为在个别词语上有所调整,但对整体几乎没有影响。如2001版《审查指南》中“.…..并且具有应用该日期之前常规实验的手段和能力……”而2006和2010版《审查指南》中均为“.….. 并且具有应用该日期之前常规实验手段的能力……”
③Guidelines for Examination in the European Patent Office (status April 2010), Part C, Chapter II, 4.1
④Guidelines for Examination in the European Patent Office (status April 2010), Part C, Chapter II, 4.1
⑤我国《专利审查指南》在对其他条款的阐述中也多次提到了“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这一概念,如支持、清楚等条款,但“充分公开”与“创造性”条款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两个条款,为简单、清晰起见,在本文中仅就这两个条款进行对比、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