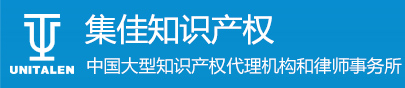- > 集佳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 > 集佳周讯 > 2025年 > 集佳周讯2025年第16期 > 法眼观察 > 销售自有商品不应落入“替他人推销”的保护范围
文/北京市集佳律师事务所 李兵
引言
第35类“替他人推销”的保护范围一直以来都是业界争论的焦点话题之一。争论的方面很多,其中最集中的争论在于零售服务是否可以通过“替他人推销”获得保护。零售服务最初没有被作为一个独立的服务项目纳入尼斯分类的保护,并且长期在许多国家不作为规范服务项目被接受,很大程度在于传统上认为零售服务就是销售商品,商品上注册商标就足够了,零售服务上注册商标没有必要性,还容易与商品商标产生权利冲突。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这种看法显然有些过时了,零售服务作为一种独立的服务种类有其专业性和存在价值。零售服务可以通过“替他人推销”获得保护在近些年的行政和司法实践中也得到了体现。
不过,随着零售服务的保护价值被肯定,似乎有从不被保护走向过度保护的苗头,突出的体现就是有观点认为销售自有品牌的商品可以被认为与零售性质的“替他人推销”构成类似,也就是“替他人推销”的保护范围也可以延及销售自有品牌的商品。这就有点儿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了。零售服务固然有其独立存在的价值和保护的必要,但是反向踏入商品商标的保护领域那就十分危险了,反而似乎印证了最初零售服务不被赋予保护价值的担忧有其合理性。
案例分析
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的《关于第35类服务商标申请注册与使用的指引》中提到:本类服务最重要的特点在于相关服务是为他人提供的,而非为权利人自身业务需求从事的有关行为。这一点在“替他人推销”这项服务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因为从文义上来讲,“替他人推销”就是推广并销售他人品牌的商品,而不是自有品牌的商品。对自有品牌的商品进行的宣传、推广和销售是对自有品牌(商标)在该特定商品上的使用,既不是在服务上的使用,更不是“替他人”。
在“OPPO及图”商标撤销复审案件【1】中,法院认为:“彪鸿公司的行为属于对‘护具’等商品及商品的商标的宣传,并非以诉争商标作为标识为不特定主体的销售行为提供建议、策划、宣传、咨询等服务。故此,相关公众针对‘OPPO’的识别仅为‘护具’等商品的商标的识别,而非指向替他人推销服务提供者。”该判决就是将商品商标的宣传行为与“替他人推销”的宣传行为区分开来,因为商标使用人对商品商标的宣传是为了销售自有商品,而非为他人提供推销服务。
在“致爱及图”商标撤销复审案件【2】中,法院指出:“推销(替他人)”服务是指为“他人”销售商品或服务提供建议、策划、宣传、咨询等服务,该类服务的对象应为商品或服务的销售者,倘若经营者以自己的名义作为销售主体销售商品或服务,则不属于“替他人推销”的范围。因此,商标注册人若主张其商标在“替他人推销”服务上进行了使用,则首先应当证明其与“他人”,即商品或服务的销售者存在商业合作关系,并为销售者销售商品或服务提供了建议、策划、宣传、咨询等服务。
在“ONME”商标撤销复审案件【3】中,法院亦指出:证据2、3主要是采购并销售ONME、NOMEI等自有品牌的商品,与诉争商标核定使用的“广告、为零售目的在通讯媒体上展示商品、进出口代理、替他人推销、替他人采购(替其他企业购买商品或服务)”服务在服务内容、服务渠道等方面不同,不属于核定服务的使用。
事实上,商品商标的使用人开设门店销售商品与零售服务提供者开设门店销售商品在服务的内容、方式、目的、场所、对象等方面有着很多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是天然存在的,因为不管是销售自有商品还是销售他人商品,都是在做商品的销售,除了商品来源不同以外,其他方面别无二致。正因如此,长久以来零售服务没有被认为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服务项目进行保护,而是将零售服务依附于商品之上。如前所述,社会实践的发展证明零售服务是有独立保护的必要性和价值的。不过,这里说到的“零售服务”是比照“替他人推销”提出的,还是为他人提供相关服务,而不是自有商品的零售。将“零售服务”与“替他人推销”类比并不全是受类似商品和服务区分表的限制,而是“零售服务”的价值就体现在将不同品牌的商品归类并统一销售。
关于“零售服务”和“替他人推销”的类似关系,最高院在“华润”商标侵权案【4】中有过论述:“虽然《类似商品和服务区分表》中第35类‘推销(替他人)’服务中并未明确包含‘批发、零售’服务,但是认定服务是否构成类似,应当以相关公众的一般注意力为标准,结合经营主体的经营范围、经营模式、服务对象等因素综合考虑。从本案来看,华润商店将自己所代理或购进的各类品牌灯饰进行归类并统一销售,以方便消费者选购,其所销售的灯饰产品显示的标识及相关信息仍来源于其代理或购进的灯饰品牌,而‘华润灯饰’系为销售上述灯饰产品所提供的服务标识。上述销售模式与涉案商标核定使用的服务存在交叉和重合,二者构成类似服务。”判决中提到,承担侵权责任的华润商店是将“各类品牌灯饰进行归类并统一销售”,“‘华润灯饰’系为销售上述灯饰产品所提供的服务标识”。也就是说,消费者在店内认牌购买的仍是“各类品牌灯饰”,“华润灯饰”指示的是销售服务的来源。这是本案将“零售服务”和“替他人推销”认定类似的关键所在。假设该案中华润商店销售的灯饰品牌就是“华润”而非“各类品牌”,那便不会再牵涉“零售服务”和“替他人推销”的类似认定,而是要依据灯饰商品上的注册商标去判定侵权。
商品商标的使用与服务必然是密不可分的,尤其在宣传和销售上,商品商标的使用很大程度上都是依靠着服务去实现的。但是,销售自有商品和“零售服务”或者“替他人推销”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前者商标使用实现的效果和商誉的承载都在商品上,而后者是在服务本身。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在“鲍师傅”商标侵权和不正当竞争民事纠纷案件【5】中提到:“服务与商品的区别在于服务具有无形性特点,且服务的产生和消费在时间上大体一致,而商品一般是有形物,商品的生产和消费在时间上有分离。本案中,鲍才胜公司以现场制售方式销售糕点符合相关行业的惯例,其制作行为与销售行为并不存在时间上的同一性或不可分离。糕点制作行为本身并没有成为可与糕点商品相分离的独立服务,进而向消费者提供,其价值均凝聚在糕点商品之上。相关消费者的直接消费对象为糕点,鲍才胜公司并不提供就餐场所以及相应的就餐服务,故消费者看到上述商标使用行为,会将该商标与鲍才胜公司销售的糕点相联系,而不会误认为是餐饮服务。”“鲍师傅”案件涉及第30类“糕点”和第43类“餐饮服务”的区分问题,复杂程度要远比区分通常的化妆品、服饰、家具等商品的销售和“替他人推销”大得多,因为这些商品的生产和消费在时间上有明显分离。只要透过服务的表象去看商标使用的实质所在,去看商标价值凝聚在哪里,消费者的消费对象在哪里,就能够将自有商品的销售和“替他人推销”清晰地区分开来。
结论
“替他人推销”的核心就在于“替他人”,不包括通过零售或者批发等方式直接向消费者出售自己的商品或者服务,单纯的商品销售行为不属于为他人推销服务范畴【6】。销售自有商品是商品商标的一种使用形式,而不是“零售”意义上的“替他人推销”。销售自有品牌的商品仅需寻求在相关商品上的注册保护即可,不必非要在第35类“替他人推销”服务上取得注册。
从权利冲突的角度而言,以“替他人推销”作为替代保护的零售服务应该与商品商标的销售行为存在清晰的权利界限。除驰名商标等特殊情形以外,不能因为服务内容、方式、目的、场所、对象等相似性,将销售自有商品的使用行为认定与“替他人推销”构成类似。否则,将会架空商品商标权利,同时将“替他人推销”的权利保护范围过分扩张。
实践中,“替他人推销”已经长期呈现与其实际保护范围不相匹配的过分注册的现象,如若再扩张其保护范围,将催生更多的非必要商标申请,同时给予获得注册的商标不恰当的超级保护,这样的“王牌服务”和“超级商标”不是健康的商标保护制度下应当鼓励的。
注释:
【1】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19)京73行初9682号行政判决书
【2】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20)京73行初8838号行政判决书
【3】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21)京行终2235号行政判决书
【4】最高人民法院(2021)最高法民再338号民事判决书
【5】北京知识产权法院(2020)京73民终2644号民事判决书
【6】国家知识产权局《关于第35类服务商标申请注册与使用的指引》